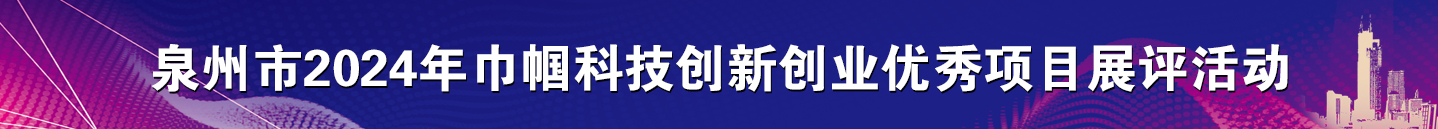“黃龍三見”與三榜眼的傳說:黃龍溪出現“龍影” 當年科舉泉州必出一位榜眼
泉州黃龍溪的水湛而深,每遇漲潮,恰似“海眼”開闔。民間傳說稱,溪上只要出現“龍影”,則當年科舉泉州必出一位榜眼。由宋至明,已有曾會、石起宗、黃養蒙三人應此讖語,故有“黃龍三見”之說。美麗傳說賦予了黃龍溪獨特的文化內涵,也表達了民間對于文教昌盛的一種向往與追求。
黃龍溪得名于唐末五代

古時黃龍溪繞流南安文廟,圖為南安文廟現狀。
泉州東溪、西溪兩大支流在南安豐州的雙溪口匯合,隨后奔涌至九日山前,此溪江段被稱為“金溪”。在其下游,即為黃龍溪(也稱黃龍江),溪水滾滾直抵如今的潘山公園南岸。潘山南麓古有黃龍渡口,今已廢。其實,現在黃龍溪的流域,與古代還是有些不同的。古時,黃龍溪是從南安文廟前繞行而過的,今因地理變遷,離南安文廟已有數百米的直線距離。沿溪風物雖有變化,但民間傳說卻世代相承。相傳,黃龍溪得名于唐末五代,當時有長史吳晝登上九日山下的高樓,意外發現山中隱有龍影,于是搭弓射之。結果一條黃龍騰空而走,山裂成溪,此溪即稱黃龍溪。明代何喬遠在《閩書》中稱黃龍溪是出于“歸化里西平、五峰二山間”,“石峽夾峙,飛流下注,水湛至深,里人指為海眼。時有龍見脊影,禱雨時應。”
古時,黃龍溪中屹立一巨石,民國時期的《南安縣志》載其“高廣幾一丈,狀如蛤蟆,頭腹并肖”,并記稱“此石有黃點,能隨水上下”,看著像是在溪中快樂舞蹈。于是這塊會“跳舞的大石”被民間稱為“黃石”。《閩書·方域志》還稱此石“舊在溪中,后移岸上,比復見溪中矣”,把這巨石描繪得像塊“活石”,使之成為黃龍溪上的一大奇觀。明清時期,因為豐水期水流湍急、聲勢浩大,黃龍溪又多被旅人稱為黃龍江。
曾會登榜眼引發傳說

曾會曾至九日山下延福寺訪契仙上人。圖為延福寺現狀。
泉州古郡,瀕臨海疆,背依群山。泉州人不僅有瀚海漁獵的智勇,也有耕讀傳家的剛韌。北宋時,泉州郡城內出了一位才子曾會(字宗元)。其父曾穆曾任德化令,殿中丞致仕。曾會少時家道中落,但他不懼貧寒,求知若渴。為了不被打擾,他常出郡城沿江獨行,借著天光誦讀詩書,時而又以草稈作筆、泥地為紙,默書胸中經論。順著筍江、黃龍江而上,有名山九日山,此山“雙峰翳翳,摩崖歷歷”,曾會也慕名前去拜謁過這座名山,后來還結識了山下延福寺住持契仙上人。
那時,同郡另一位才子錢熙(豐州人)與曾會關系不錯,兩人常同席課讀。雍熙二年(985),錢熙率先擢進士,于是他寫詩句鼓勵曾會曰:“好看閩州名士傳,東南此事古來稀。”這番話點燃了曾會心中的火種,他更加刻苦攻讀,以期追趕好友的步伐。端拱元年(988)秋,曾會參加福建鄉試,力拔頭籌,成為當年解元。返鄉之后,曾會特地入住九日山下的延福寺,試圖在梵宇琳宮中靜下心來讀書,為明年的春闈做準備。結果,翌年,曾會果真金榜題名,殿試居甲科之二,成為“榜眼”。
消息傳至家鄉,整個泉郡都沸騰了。有人便順勢附會稱,這是黃龍溪中的“黃龍”開眼了!也有聲稱,就在曾會登甲第時,有“黃龍見溪南”(見《閩書·方域志》)。民間有傳言稱“溪南”是指金雞渡渡口,也有稱是在黃龍渡口,不一而足,但都表達出一種對家鄉出了英才的自豪、亢奮之情。
端拱二年(989)十二月,曾會請假還鄉。淳化元年(990)三月,在攜家眷入京時,曾會又至延福寺訪契仙上人,并為該寺撰寫《重修延福(寺)碑銘》,留下重要歷史信息。曾會育有六子,其一便是北宋名相曾公亮。曾會一生著述頗豐,傳世的有《雜著》20卷、《景德新編》10卷等。清道光《晉江縣志》載:“以文章名世者,唐有歐陽行周(歐陽詹),宋有曾宗元(曾會),文藻敏給。”
志怪小說描繪“見龍”場景
如果說北宋曾會的“榜眼之路”僅是為“黃龍現蹤”傳說提供了某些靈感的話,那么南宋石起宗的科舉事跡,則為宋人創作黃龍溪“民間故事”提供了重要素材。
石起宗,字似之,祖籍同安。北宋時,同安石氏為望族,曾出過石亙、石賡等名臣。石起宗后來隨家人先后徙居晉江安海、泉州郡城。少年時,石起宗曾讀書于晉江靈秀山中。他好學不倦,特別嗜書,故而學問扎實。徙居泉州城的萬厚鋪(故居原址在今井亭巷內)后,石起宗從學于名師黃宙(即黃由仲),在詩賦、書畫等方面皆有造詣。當時城內住著一位名士,名喚諸葛廷瑞(字麟之)。因在萬厚鋪有諸葛氏的祠堂,諸葛廷瑞經常出入萬厚鋪,由是與石起宗也熟絡起來。雖然諸葛廷瑞比石起宗大11歲,但這毫不影響他倆成為摯友。二人經常相互切磋學問,增長學識見聞。諸葛廷瑞祖籍是南安,他對九日山也很熟,于是常拉著石起宗往九日山上跑,既覓前賢蹤跡,也觀山秀婉麗。乾道元年(1165)秋,二人還與友人同登九日山,并留下石刻一方。惜今石刻上部分字跡早已漫漶不清。
乾道五年(1169),石起宗與其師黃宙一同入京參加會試,雙雙金榜題名。而后在殿試時,石起宗更是勇奪榜眼,入列甲第。實際上,乾道五年,泉州中進士之人多達19名,史稱“溫陵得人為盛”,成為全國美談。時任泉州太守的王十朋,聞訊大喜,當即在州衙內的忠獻堂為新第者贈詩曰:“四海英才入網羅,清源龍虎姓名多。經魁蘭省得人杰,策射楓庭收甲科。奎宿呈祥前未見,緯星還舍首相過。一杯忠獻堂中酒,名節相期要不磨。”之后,為鼓勵石起宗,王十朋又作一詩《贈第二人石察判》曰:“策冠諸儒已奏聞,不妨居次避平津。坐看萬石門闌大,轉覺朋山氣象新。黃卷更窮稽古力,青云莫負致君身。試觀忠獻堂中像,亦是當時第二人。”當時忠獻堂內塑有歐陽詹、曾會、韓琦之像,他們皆為科舉“第二人”(即榜眼)。王十朋通過詩句暗示石起宗,日后也要向幾位先賢看齊。
或許是這次乾道五年的泉州科舉大捷太有名了,讓一向關注于“神奇荒怪”的南宋文學家洪邁也“聞風而動”,搜集起與這次事件有關的信息。這一搜不要緊,還真就搜出了有趣的故事。洪邁在其《夷堅志·丁志·卷11》中寫道:“泉州南安縣學前,有溪名‘黃龍’。乾道四年,(南安)邑令天臺鹿何趨府歸,過學門,聞路人喧呼,轎卒皆駐足驚顧。怪問之,曰:‘黃龍溪上龍見。’鹿停車熟視,波瀾洶涌中,一物高數丈,嶄然頭角,出沒其間。須臾雷聲大震,煙霧蔽蒙,騰空而上,人多有見其尾者……”南安縣令鹿何與一批“吃瓜群眾”,竟然在乾道四年親眼目睹了黃龍溪上“黃龍現蹤”。乾道三年至四年,鹿何一直在主持修繕南安文廟,所以他經常要路過黃龍溪。《夷堅志》還記載了鹿何“見龍”后為安慰諸生所作的詩句:“雞渡已符當日讖,龍溪仍見此時祥。”前半句指的正是曾會高中榜眼時,民間傳說金雞渡外的出現“龍影”。沒承想,就在黃龍溪上“見龍”之后的一年內,石起宗也成了榜眼。《夷堅志》于是斷言“龍之為靈,其非偶然”,該書不愧是古代著名志怪小說,很懂如何吸引民眾眼球。
“黃龍三見”頗具傳奇色彩
“黃龍現蹤”故事在明代仍有延續,而且目擊者同樣人數眾多,而這次“見龍”對應的事件則是黃養蒙高中榜眼。
黃養蒙,字存一,號小竹,南安豐州燕山人,廣東按察僉事黃澄之子。黃澄對家族子孫的教育十分嚴格,他在為官之后,為讓家族延聘的塾師更好地督導子孫學習,特地在豐州九日山的東臺重修“九日山書室”(亦稱半山書屋),嚴令兒子養蒙等人入室苦讀,風雨無阻。養蒙晚年重訪九日山時,還寫下《九日山書室》一詩以紀念這段日子:“曾楹茅屋九山曲,時望金溪小徑通。堆葉掃云尋老子,烹茶讀易夢周公。幾年司計慚明主,何日乘舟掛晚蓬?江上清風猶舊否,沙汀為我問漁翁。”功夫不負有心人,黃養蒙在明嘉靖二十年(1541)春闈時考中進士,殿試擢為榜眼。

今九日山登臺廟所在位置即為黃養蒙讀書處(九日山書室)舊址
何喬遠在《閩書·方域志》載:“皇朝嘉靖二十年春,(南安)邑人鄭普與節推葉遇春飲清源山。葉遙指此溪曰,時大雨中隱隱若龍起西方者。群下咸曰:‘有之!’語未竟,春榜報至,則黃養蒙又舉為第二人。”葉遇春(號素峰)、鄭普(南安名士)等人某天正在清源山飲酒話仙時,葉氏突然見到山下黃龍溪一帶有“龍影”浮現,而且手下之人也都目睹了這一“祥異”事件。更奇特的是,就在他們驚魂未定時,黃養蒙登甲第榜眼的喜報即至,這種本應電視劇里才有的橋段,偏偏也出現在《閩書》這樣的古代文獻中。數年后,嘉定人唐愛(字良德)出任南安縣令,有人將這一情況反映給他。唐縣令一聽樂了,馬上跑到養蒙讀書的九日山書室外,題寫“黃龍三見”四字。鄭普還為這題詞寫了一篇長長的跋文,詳述當時“見龍”的情景。只不過罕有人知道的是,唐愛恰巧也是嘉靖二十年進士,養蒙登甲第時,他就在現場。

鄭成功焚青衣處與南安文廟近在咫尺

今見龍亭小區一側
嘉靖二十八年(1549),唐愛主持修繕南安文廟。當時在南安文廟的東面,有一座宋代建的云泮橋(拱橋),年久失修。唐縣令于是下令將此橋改建為長橋,“其狀如龍,向黃龍江而出”,意圖呼應嘉靖二十年的“見龍”事件。隆慶二年(1568),泉州府同知丁一中又在此橋南邊筑亭,“以象龍首”,這座亭子被取名為“見龍亭”。橋、亭今均已無覓,但原址即在如今的見龍亭小區一帶,附近另有“鄭成功焚青衣處”古跡。
黃養蒙登甲第后,南安即在縣治前為黃澄、黃養蒙父子立下“父子進士坊”;后來,黃養蒙官至吏部郎中時,又在縣南門內為其立“天官坊”一座。泉州城內,明時在中華鋪為黃養蒙等人立有“辛丑進士坊”;后又在肅清門內清平鋪,為黃養蒙(時任戶部侍郎)立了一座“會魁坊”。黃養蒙沒有辜負家鄉人的期望,為官之時,他“器度過人”“歷官有聲”。在南安,他還參與倡建南安新城,改建武榮慈濟真人廟,以及組織民眾疏通修復重要水利設施萬石陂。隆慶二年(1568),泉州知府萬慶聘請傅夏器、尤烈、朱安期、趙恒等人纂輯而成《泉州府志(隆慶本)》時,尚書黃光升與侍郎黃養蒙是該志書的總裁。
“龍影”也曾藏在巷井之間

黃龍渡口已化作蒼茫荒野
而今黃龍溪上屹立起了黃龍大橋,橋上每天行人如織、車輛熙攘穿梭。昔日人聲鼎沸的黃龍渡口,業已化作蒼茫荒野。自從有了“黃龍三見”之后,黃龍溪上再未有人聲稱目睹過“龍影”。神奇的傳說故事,在永恒的時間面前,悄然“合龍”。
不過,黃養蒙在自己晚年時留下的一篇文章卻與“龍”有關,那就是《南安縣龍須巷雙井修復刻石記》。文章大意是說在南安豐州古有二巷名為“龍須”,另有雙井為“龍眼”。可惜時間一久,“二巷為民居所侵,僅存尺許,淖穢傾積,不可以行”。“龍眼”是東、西兩口井,東井名為“九龍井”,西井因有民屋建于其上,“漫沒已久”,連井名都不得而知。隆慶二年,廣東人邱凌霄出任南安縣令后,重辟龍須巷,而后疏浚東井,又新鑿西井,“井泉冽而上出,老幼嗟嘆,以為大觀”。這篇文章也算是為南安豐州關于“龍的傳說”,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。
責任編輯:蘇慧敏
1、本網站所登載之內容,不論原創或轉載,皆以傳播傳遞信息為主,不做任何商業用途。如因作品內容、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,請在30日內進行。
2、本網原創之作品,歡迎有共同心聲者轉載分享,并請注明出處。
※ 有關作品版權事宜請聯系:0595-22128966 郵箱:admin@qzwhcy.com